柳焜昱从前也是个不太好相与的性子。
他和庄子瞿的区别,大概在于他比较安静,不太会主动惹事。
但只要庄子瞿想干什么坏事儿了,只要来找他,他就一定会跟着一起。
柳焜昱出身皇室,再加上天资聪颖,修炼上顺风顺水。八岁引气入体,十一岁筑基,十五岁结丹,除了少数的那些人,谁也不放在眼里,谁也不在意。
这些人概括起来也不过家人,师傅师弟,还有一个庄子瞿。
他就如他的名字,“焜昱错眩,照耀辉煌”,从来都是一颗耀眼无比的太阳。
太阳怎么会在意萤萤星光。
二师弟笙咏桂在他十一岁那年上的山,三师弟晚一些,彼时他十五,没过多久就结了丹同庄子瞿一道游历去了。
庄子瞿结丹比他晚些,不过他同时还得学医毒,学阵法——这些都是归澜门专精的几项,柳焜昱倒也不是没有学些杂七杂八的,只不过大都涉猎,学着玩而已。因为他脑子好,学什么都快,学着便很快就会觉得无趣。
两个少年从东边的羲和门出发,一路南下途经了风情各异的地域,长了不少见识,奇怪的技艺也学到了不少。
柳焜昱甚至还记得,在南方的时候两个人现学了水乡方言,挨个儿去茶楼说书,当时他们还拿自己一个月的伙食打赌——输的那位需包了两人接下来一个月的饮食开销——赌谁人气更高。
不过最后也没分出个胜负。
两个人刚学了几成吴言软语,没来得及实践,就不得不离开。
那时柳焜昱十六。
他心中尚明确了什么是他想走的道,什么是匡扶正义。
只不过变故生的突然,他倒底是跌了跟头。
风吹雨洗一城花。
江南的秋季总有连绵的细雨。
雨如烟如纱,整日整夜的下,雨珠连成线从檐角落下,敲在青石板路上,发出规律的撞击声,于凉夜催人入睡,又扰人无法安眠。
而少年人的朝气是不会被这点淋个半天也无伤大雅的蒙蒙烟雨所浇灭的。
穿着青衣的少年一头长发全部束起,看上去清爽干净,他执了一把油纸伞站在客栈门口,半未撑开,像是在等人。
约莫站了半刻钟,木制楼梯忽被踩得踢踏乱响,半扎发的绛衣少年风风火火地从上面掠了下来,冲向门外。门外的少年轻叹了口气,习以为常般地率先步入雨帘。
“等等我啊!”绛衣少年嬉皮笑脸地追上去,熟练地揽过好友的肩,“走那么快干什么。”
青衣少年不作声,只抿了抿唇,也不看他。
“阿昱?柳焜昱?理我一下啦。”
他自讨没趣,用空着的那只手摸摸下巴:“我也不是故意让你等那么久的呀……”
柳焜昱咬牙切齿:“你还是初犯吗?这一月走来,日日如此……庄子瞿,你夜间到底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去了,日上三竿都起不来!”
“哎呀,”他心虚的笑了笑,不过未让柳焜昱发觉,一边熟练地哄人,“下次不敢了,真的。”
庄子瞿在他瞧不到的角度,下意识地瞥了眼自己的储物法器,偷偷勾起一个笑。
毕竟明天起就不必再通宵了,所以也不必为了避免被挚友瞧出来,得先拿灵力调节好自己的精神气再出门了。
柳焜昱知道他是一旦作出保证就不会食言的性子,面色稍缓,轻哼一声算是揭过这事。
“话说,”庄子瞿懒懒散散地过他手中的伞撑开,此时雨不大,但因着有风,所以细细密密地直往人眼中撞,没走几步就糊了满眼,令人怪不舒服的,“我俩的比赛还没比完,怎么今天就急着走?”
他提着嗓子,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方言学吴地小姑娘们娇声说话:“小郎君,一天都等不了哇?”
柳焜昱被他逗乐了,唇角的弧度上扬了些
不过很快就像想起了什么,又耷拉了下来。
“是昨夜……”两个人已经行至渡口,踏着烟雨同河水交融而漫出的雾气,登上了柳焜昱今日清晨出来订好的船。
他接着说了下去:“我昨夜收到兄长的急书,让我速归。”
“旁的却只字未提……”
他迟疑着,停下了话头,
“子瞿……我有不太好的预感。”
修道之人多少有些通连天地,他们的这种“感觉”并不完全称得上空穴来风。
甚至有时不容忽视 ……“阿昱。”庄子瞿一下子意会到了他的想法,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提醒他,“你的兄长既然会给你来信,说明事态并非无法控制,否则他应该会让你别回去了。”
柳焜昱哪里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也是他至今还能用平静来掩饰自己的原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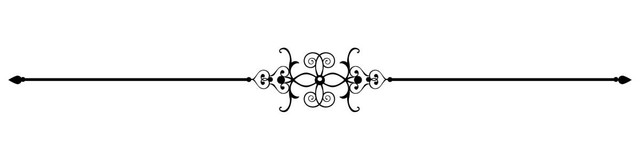
“浮云郁兮昼昏,霾土忽兮塺々。”
出自两汉王褒的《九怀》。
“焜昱错眩,照耀辉煌。”
出自《淮南子·本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