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再次到来,1865年不可避免的来了。
“您为什么不说呢。”我把饭放在山南敬助面前,“好好的,您干麻要逃呢?”
山南敬助只是温和地笑了笑:“没必要了。”
“您是因为要躲避战乱吗?还是因为对新选组不满什么的?”
他皆摇头:“都不重要了…”
元治二年,也就是1865年二月,山南敬助因脱队的罪名判以切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逃。在近江国大津,冲田君找到他时,他显得很平静。
二十三日,开始执行,由冲田君执行“介错”。这也是山南所希望的。
“为…为什么!”伊东甲子太郎摇着我的肩头,“只是因为如此便要山南切腹吗?他是如此优秀,他对新选组是绝对的忠心啊,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吗?”
“我们都知道,但…这是规定。”
“规定?哈哈哈哈…好一个规定!”伊东甲子太郎狂笑着,他怨恨的目光让人心惊,“新选组…壬生狼…不过一群没有心的杀人工具罢了。”
山南敬助切腹时,伊东甲子太郎没有去,我亦没有去。
“冲田君…结束了么?”我起身,迎上冲田君。
“嗯。”他看起来很疲倦,往日轻松的笑容掩了起来,血溅了他一身。
“山南先生,怎么会逃跑呢…”我发出最后的质疑,山南敬助的死,太突然了,虽然史书上有记载着,但我也只是粗略地瞅了眼,并无多大印象。
冲田君苦笑:“谁知道呢…”
山南敬助的死,至今我也不明白,尽管知道翻翻史书便能知道的事,我依然没有去翻,为什么呢?是因为山南先生不想让我们知道吗?
山南敬助的死,使新选组不仅失去一位优秀的总长,更失去了,某些队员的心。
“诱惑春风吹来的山樱,散落之后被人怜惜。
因风而凋零的山樱,花散勇犹存。”
“这…是伊东先生写给山南先生的吗?”听到有人在吟诵,我还是犹豫地问了一下。
伊东甲子太郎有几分惊讶地转身:“哦,柳啊…”
“…您经常来这里呢。”我上前,将一束鲜花放在墓上。
“你觉得…新选组怎么样?”他问。
“新选组?我很喜欢这里。”
“哪怕…这里是修罗场?”他冷笑质疑。
我一时无言,半晌,才道:“…土方先生并没有那么无情无义…只是…严了些罢了。”
伊东甲子太郎瞥了我一眼:“也许吧。”
“冲田君,土方先生是不是很严格呢?”我趴在窗前,望着冲田君擦剑。
他没有犹豫,边笑边擦:“不可否认,土方是我见过最严格的人了。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副局长,不是吗?”
“嗯。”
“今天好不容易不训练,你…去看看平助吧…他最近…有点颓丧。”
“是因为山南先生吗?”我轻声问道。
他只是笑了笑。
“平助?我进来了?”我都不用猜,便知道藤椅平助又卧在被子里。
“…”没有回应。
“嗯?”难不成藤堂平助不在宿舍?
我推门而入,并没有想像中的空无一人,藤堂平助果然缩在被子里,肩头一耸一耸的。
“平助?”
“嗯。”他闷闷地应了声,有很重的鼻音。
自从山南逝世,藤堂平助便一直这个样子。
“…你别太难过了…”我不会安慰人,这个时候我能说的,也仅止于此了。
藤堂平助缓缓坐起,双眼红肿,小声呜咽。
说倒底,按我在日本现在的年龄,藤堂平助比我还要小两岁,只能说还很年轻,说小也不为过了。
“樱楠,我知道,山南先生犯了队规,必须切腹,可是…山南先生才刚去世没多久啊…副长…副长便要把屯所迁到西本愿寺北集会所…”
“迁至西本愿寺北集会所?”我大吃一惊,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只是有个大体印象,但竟然是在山南敬助去世不久?
“你听谁说的?”我忙问道。
他脸上没有以往愉悦的笑容了,他难过道:“土方亲口说的,我听见他和近藤先生的谈话了。”
“这…我去问问吧…你不要太难过了。”
我敲了敲门。
“谁?”
“土方先生,我是柳樱楠。”
半晌,他才道:“进。”
“说吧,什么事。”他喝了口茶。
我绞了绞衣角,还是道:“在下听说…要把屯所迁至西本愿寺北集会所?”
土方岁三点了点头:“没有错。你的消息倒是灵通。”
“山南先生才去世这几天,这便迁所,不是大不敬吗?”我质问道。
“那你又想如何呢?屯所实在太小太小了,队员越来越多。晚迁一天,便不利一天。如果山南知道的话,他会赞同我的话的。”
“您知道…大家对您很不满吗?”
“不满?他们不满又能如何呢?身为武士,不应该把所有的情感都抛之脑后吗?”
“是,我知道了。”我微微点头,身为现代人,我倒是对如此礼节不甚在意,既然土方岁三都如此说了,我也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等一下。”
“嗯?”我看着土方岁三。
“告诉藤堂,我很抱歉。”他不知何时,已经转过身去了,但脸上的漠落难以掩示。
“是。”我点了点头,缓缓退了出去。
题外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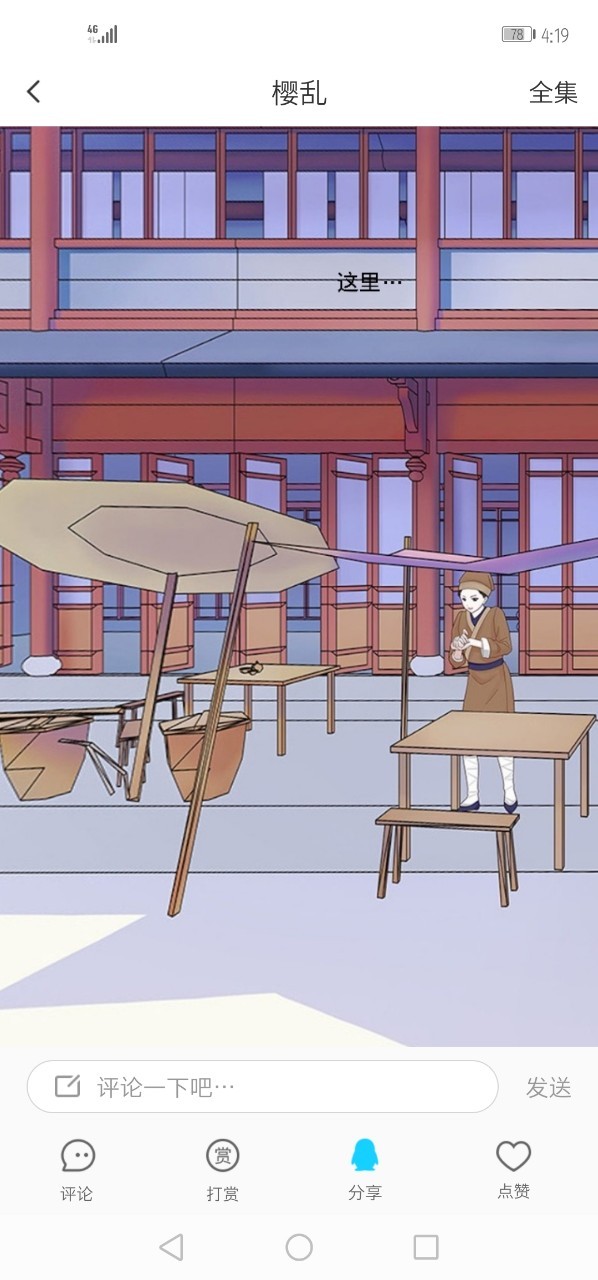
















小元子作者你脸呢,文字还没有图片多。